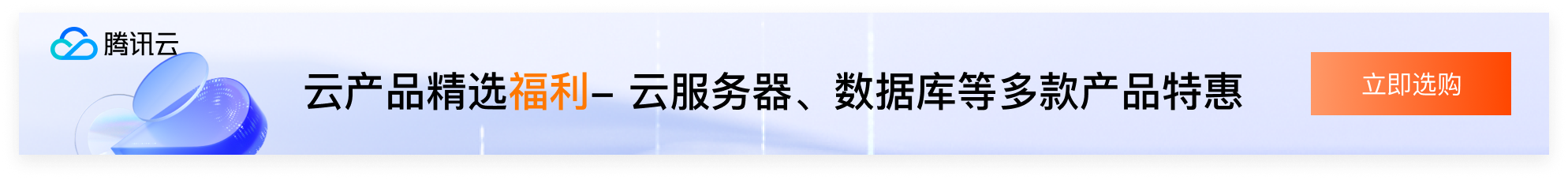AI摘要
回头想想自己六年前的代码,会觉得有些“羞耻”,但又倍感亲切。那时候,我刚从一个能熟练使用SSH框架完成功能的“菜鸟”,升级为一个能独立负责一个完整模块的“模块开发者”。我当时的全部骄傲,就在于我写的模块bug少,逻辑清晰,代码规范。
我的世界,边界就是接口文档上定义的输入和输出。上游是谁?下游是谁?系统瓶颈在哪里?未来的扩展性如何?这些问题,似乎都有一个叫“架构师”的遥远角色替我考虑周全。我就像一个技艺精湛的木匠,能完美地打造出图纸上要求的每一个橱柜和房门,但从未思考过整个房子的结构承重和动线设计。
转变并非一蹴而就,也并非源于某次轰轰烈烈的生产事故。它发生在无数个平淡的日常开发瞬间,源于那些让我感到“别扭”和“困惑”的细节。这篇文章,就是想分享这段“静悄悄”的成长。
第一阶段:困惑源于“疼痛”
最初的几年,我的工作模式是“任务驱动”。产品经理提出需求,技术负责人(或架构师)将需求拆解成任务,我领走属于我的那几个,然后开始编码、测试、交付。我一直觉得这很高效,直到我一次次地陷入同一种“疼痛”。
疼痛一: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的恐惧
我记得最清楚的,是一次看似简单的需求:为某个核心实体增加一个状态。按照习惯,我找到对应的枚举类,新增了一个状态值。但随后,我惊恐地发现,我需要修改至少五六个相关的Service类,因为每个类里都有对该枚举的状态判断。这还只是后端,前端同事也跑来问我:“你这个新状态,之前的几个页面该怎么展示?”
那一刻,我感到了深深的无力。我只是加一个状态,为什么像推倒了一排多米诺骨牌?我开始怀疑,问题不在于这次修改,而在于最初的设计。如果这个枚举承载了过多、过于分散的业务逻辑,那么它本身就是不稳定的。一个良好的设计,是否应该将状态变化带来的影响收敛在一处?
疼痛二:“重复劳动”的厌倦
另一个项目里,我负责用户中心和订单中心两个模块。我发现,两个模块里都有非常相似的地址管理功能。我几乎是复制粘贴了代码,只是改了改包名和数据库连接。一开始,我觉得这很“快”。但很快,当业务方要求给地址增加“经纬度”时,我需要在两个项目里做完全相同的事情:改DTO、改Mapper、改Service。
我开始问自己:这真的“快”了吗?如果未来有十个服务需要地址功能,我就要重复十次?这种重复,不仅浪费生命,更是埋下了巨大的维护隐患。总有一天,这两个功能的逻辑会因为各种微调而变得不一致,从而产生诡异的bug。
第二阶段:破局始于“偷师”与“模仿”
疼痛迫使我抬头看路。我不再满足于仅仅完成我那一亩三分地的任务。
1. 我成了“代码考古学家”
我开始带着问题去阅读团队里公认的“大神”写的核心代码。我不再只关心“他怎么实现这个功能的”,而是问自己:
- 为什么他把这个类放在这个包里?包之间的依赖关系是怎样的?
- 为什么他要定义一个抽象的
BaseService,里面似乎没多少代码? - 为什么他要用一个看似复杂的
Strategy模式来处理这个业务,用几个if-else不是更直接吗?
比如,为了解决我那个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的枚举问题,我看到了他是用State(状态)模式来处理的。将每个状态的行为封装在独立的类中,状态变迁带来的逻辑变化被完美地隔离了。这次阅读像一束光,照进了我漆黑的设计思维小屋。原来,代码可以这样组织来应对变化。
2. 我成了“文档贪婪者”
公司的架构文档、技术方案评审会议,我不再是那个沉默的听众。即使很多内容当时听不懂,我也强迫自己去听、去记。会后,我会拿着不懂的术语(比如“领域驱动设计”、“六边形架构”、“CQRS”)去查资料、看博客。我会把看到的理论,试图和我们项目的代码结构对应起来,思考:“哦,原来我们项目里的这个order-core模块,就有点像DDD里的领域层?”
这个过程非常痛苦,就像在拼一张没有参考图的巨大拼图。但慢慢地,一些碎片开始连接起来,我眼前模糊的“系统全景图”逐渐有了轮廓。
第三阶段:实践与小的胜利
光看不练假把式。真正的成长,来自于在具体工作中创造机会去实践。
我的第一个“系统设计”练习:解耦重复的地址功能
面对那两个重复的地址模块,我决定做点什么。我没有权力直接要求订单服务调用用户服务,但我可以做一个“技术提案”。
我花了一个周末,写了一份简单的设计文档。文档里:
- 提出问题:清晰地展示了当前代码重复的事实,并推演了未来维护的成本和风险。
- 提出方案:建议将地址功能抽离成一个独立的Jar包,定义清晰的API和数据结构。
- 分析利弊:好处是代码复用、统一维护;代价是项目间依赖加强,需要一套版本管理机制。
- 制定迁移计划:如何逐步将用户中心和订单中心的地址功能平滑迁移到新Jar包,而不影响线上业务。
周一把文档发给我的导师和技术负责人后,我紧张地等待着。结果出乎意料,他们非常支持。不是因为我的方案有多完美,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在主动思考系统性问题,并尝试推动解决。这次小小的成功,极大地鼓舞了我。它让我明白,系统设计能力不是被“授予”的,而是通过主动思考和承担责任“赢得”的。
从此,我养成了一个习惯:在接到一个开发任务时,不再是立刻动手敲代码,而是先画图。用笔画一画模块之间的关系,找找潜在的耦合点,思考一下未来可能的变化点。我开始尝试在代码中引入一些简单的设计模式,不是为了炫技,而是真的为了让代码更能应对变化。
结语:视角的转变
六年后的今天,我依然在编码,但编码在我工作中所占的比重和意义已经完全不同。以前,编码是目标,是工作的全部。现在,编码是实现设计的手段,是验证我想法的最后一步。
我从一个只关心“点”(我的模块)的开发者,成长为一个开始关注“线”(模块间交互)和“面”(系统整体架构)的设计者。这种转变的核心,并非掌握了多少种高深的技术框架,而是一种思维模式的升级:从实现逻辑到管理复杂度。
我不再惧怕那些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的修改,因为我在设计时就已经为“变化”留好了位置。我也不再厌倦“重复劳动”,因为我会本能地去寻找抽象和复用的机会。
这条路还很长,六年只是一个开始。但我知道,只要保持对“疼痛”的敏感,保持“偷师”的好奇心,并勇敢地抓住每一个实践的机会,我们都能一步步成长为那个能为自己和团队“绘制蓝图”的人。